1月19日,记者离开遵义,沿川黔公路北上,当晚如期抵达35公里以外的泗渡镇。回想起在市区采访的12个日夜,我们百感交集,心潮澎湃。
70年前,日臻成熟的党中央和军委在遵义会议后,既坚持实事求是,肯定了通道会议以来的正确思路;同时又从实际出发,看到黔北敌情严重,经济落后,就放弃了原来想“以遵义为中心,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”的意向,接受刘伯承、聂荣臻等人的建议,决定“红军渡过长江,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”,以更好地适应北上抗日的形势和要求。1935年1月19日,中央和军委纵队离开遵义向北挺进,当日抵达泗渡镇。
今年1月19日上午9时20分,记者按照相关约定,赶到遵义会议会址前。1月7日我们采访会址时担任解说的小李妹妹,听说记者要离开,立即从纪念馆里跑出来送我们。这时,从会址前经过的路人纷纷驻足。有的托起记者的背囊一试轻重,有的展开“重走长征路”的队旗轻轻抚摸。
10时许,在一座大桥旁,记者遇上了迎亲的车队。新郎却示意司机停车,并摇下车窗,一脸笑意让我们先行。过桥后,桥东侧的音像店老板看着我们走近,立即高音量地播出了《十送红军》:“一送……红军,……下了山……”
一路走来,一路激动,不知道和多少遵义人握手话别,不知向多少英雄城的市民招手致意。感到脸上有凉意时,记者已是泪湿双颊。将要走出市区时,《遵义晚报》的两位记者闻讯后又打的赶来,与我们合影留念。一位小贩“拦”住去路,执意要送上几盒香烟。当我们推辞说不抽烟时,他一脸愕然地说:“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后,早就想好了要送你们几盒烟。再往北走山多,一路保重啊!”
泪别遵义,思绪万千。在遵义采访的12天里,新乡的军地领导没有忘记千里之外的牧野赤子,委派专人前来看望我们,让我们在南国的寒冬里,感受到了来自故乡的温暖,更使兄弟长征队的同道,对此羡慕不已;遵义市委宣传部、党史办的同志们,对我们的询问耐心指教,提供资料时倾其所有;《遵义日报》和《遵义晚报》的同行,在我们上网不便时,积极提供传稿便利,并对我们出发至今的活动,作了多侧面、多角度、长达3000多字的报道;记者下榻的湄江招待所的服务员们,想方设法为记者提供生活上的便利,使我们有宾至如归之感。这一切,都已溶入我们的记忆,将化为我们对遵义的深切怀念和长征路上的不竭动力。
当年红军离开遵义时,万千百姓箪食壶浆,十里相送。肩负北上抗日重任的红军,由于长征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而士气振奋。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,我3万将士在30多万敌军重围下,纵横驰骋。四渡赤水,演出了一幕“用兵真如神”的威武雄壮的话剧。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说: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,有助于他们把一次可能会是士气低落的撤退,转变为一次精神振奋的胜利征程。历史表明,他们强调这一点儿是对的,在很大程度上,它决定了这次英勇远征的胜利结局。”今年2月份,红军二渡赤水后再占遵义70周年时,我们将再返回采访。
遵义,我们还要回来。
70年前,日臻成熟的党中央和军委在遵义会议后,既坚持实事求是,肯定了通道会议以来的正确思路;同时又从实际出发,看到黔北敌情严重,经济落后,就放弃了原来想“以遵义为中心,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”的意向,接受刘伯承、聂荣臻等人的建议,决定“红军渡过长江,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”,以更好地适应北上抗日的形势和要求。1935年1月19日,中央和军委纵队离开遵义向北挺进,当日抵达泗渡镇。
今年1月19日上午9时20分,记者按照相关约定,赶到遵义会议会址前。1月7日我们采访会址时担任解说的小李妹妹,听说记者要离开,立即从纪念馆里跑出来送我们。这时,从会址前经过的路人纷纷驻足。有的托起记者的背囊一试轻重,有的展开“重走长征路”的队旗轻轻抚摸。
10时许,在一座大桥旁,记者遇上了迎亲的车队。新郎却示意司机停车,并摇下车窗,一脸笑意让我们先行。过桥后,桥东侧的音像店老板看着我们走近,立即高音量地播出了《十送红军》:“一送……红军,……下了山……”
一路走来,一路激动,不知道和多少遵义人握手话别,不知向多少英雄城的市民招手致意。感到脸上有凉意时,记者已是泪湿双颊。将要走出市区时,《遵义晚报》的两位记者闻讯后又打的赶来,与我们合影留念。一位小贩“拦”住去路,执意要送上几盒香烟。当我们推辞说不抽烟时,他一脸愕然地说:“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后,早就想好了要送你们几盒烟。再往北走山多,一路保重啊!”
泪别遵义,思绪万千。在遵义采访的12天里,新乡的军地领导没有忘记千里之外的牧野赤子,委派专人前来看望我们,让我们在南国的寒冬里,感受到了来自故乡的温暖,更使兄弟长征队的同道,对此羡慕不已;遵义市委宣传部、党史办的同志们,对我们的询问耐心指教,提供资料时倾其所有;《遵义日报》和《遵义晚报》的同行,在我们上网不便时,积极提供传稿便利,并对我们出发至今的活动,作了多侧面、多角度、长达3000多字的报道;记者下榻的湄江招待所的服务员们,想方设法为记者提供生活上的便利,使我们有宾至如归之感。这一切,都已溶入我们的记忆,将化为我们对遵义的深切怀念和长征路上的不竭动力。
当年红军离开遵义时,万千百姓箪食壶浆,十里相送。肩负北上抗日重任的红军,由于长征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而士气振奋。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,我3万将士在30多万敌军重围下,纵横驰骋。四渡赤水,演出了一幕“用兵真如神”的威武雄壮的话剧。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说: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,有助于他们把一次可能会是士气低落的撤退,转变为一次精神振奋的胜利征程。历史表明,他们强调这一点儿是对的,在很大程度上,它决定了这次英勇远征的胜利结局。”今年2月份,红军二渡赤水后再占遵义70周年时,我们将再返回采访。
遵义,我们还要回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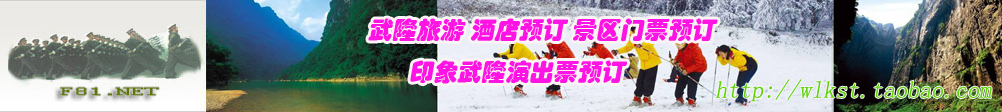
 您现在的位置:
您现在的位置: 


